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阿诺拉,都拿这个奖了,总有些什么原因的对吧。于是花上两个多小时时间看完,总体来说,不喜欢,电影名叫 阿诺拉,但是实际电影剧情的主题,拍摄的主体,貌似并没有能够让人共情上女主。像是导演带着一种刻板影响所拍摄出来的电影,有些故意,有些明显的表述,带上一些滑稽感,拥有一种不现实感,又可能是导演故意为之,让人反思思考,这个电影最终其实是在讽刺,讽刺社会,讽刺群体,讽刺不同阶级,讽刺SexWorker的渺小。还有一点让剧情掉价的情节,就是导演很可以的去让igor和ani两人同框,从第一次之后,每次同框我就想很纳闷的质疑,导演有意让他们同框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俩有感情?igor产生了同情心理?你一个打手产生了对目标的同情心理,然后对上级的背叛?这一却拍的就很有不合逻辑的地方,特别是他俩同框的画面,就有种低俗尴尬的感觉袭来,就虽然在拍摄上就像是在拍摄纪录片一样,但是这是一种带着喜剧/悲剧内核,充满不现实感觉的纪录片。我感觉换一种角度拍,观影上会更容易让观众对女主共情。但是导演的目的貌似并不是这个,他想要的并不是让观众共情女主,去体会女主所经历的,而好像是故意要让女主这个行业的人群而非个体展现的行为去向观众表现出真实一面,告诉观众SW这些人群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她们有自己的心理目的与生活,她们的群体是这样的,像是更多的一种介绍,一种剖析,没有了对某个人物的细细的刻画,虽然电影名是叫阿诺拉,电影从一开始就在逐渐刻画阿诺拉,但是越到后面,观众越来越容易从阿诺拉的视觉脱离,成为了第三者,已经各种剧情上的不合理之处......
Ivan的母亲对ani的威胁,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不合理感,以及ani就那么顺理成章的放弃了威胁,不知道她是想通了还是什么。从一开始的对这一切抱有期待到最后的放弃,从一开始她就不该心存幻想,导演可能也想表达这个。sw的经历的所遇到的,请你们就当错一场幻境,你们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不知道导演是否有特殊的隐喻在其中,比如igor的这个矛盾的角色,莫名其妙的镜头,突如其来的关心和理解,oh shit , 真是俗到极点的剧情啊。igor这个人物刻画的真的太烂了,特别是导演貌似好像还让他俩能相爱似的,是想告诉观众,这部电影实在讽刺阶级,一个sexworker一个bodyguard你俩在一起才是可能的,你俩谁都不可能跟富二代在一起的,真是shit到了极点。 igor完全没必要刻画出这种人物形象,从一开始控制ani开始,igor这种thug就表现的像是乖乖男,甚至对ani动手是又有种怜香惜玉,表情特地表现得懵懂沙楞,就像是在像女主示弱/示爱? 导演特地在拿镜头与感情在做对比,但是引入的igor这个人物与ani 和 ani与Ivan 两队做对比就很差。 Ivan 与 ani 无非同框就是 性爱 与 玩乐 。而igor 与 ani 虽然没有性爱,却有谈心的目的,有闲聊,有理解。 导演可能有意想表示 ani作为一个sw 也回去筛选自己的目标而不是选择真正的感情,她们选择感情的方式就像在夜场选择自己的猎物一样,不是去选择爱,而是选择money。但是如果真是把igor和ani搞成真爱的话实在是俗不可耐.......
点评下最后两场戏,igor 带 ani 坐飞机回豪宅,igor 看 ani 睡觉铺上衣服,明显有些示爱了,igor与ani闲聊,点烟都直接点两根,可见igor并不是只是欣赏ani,igor与ani道晚安。聊天中途可见,如果igor是真对ani有好感,那么他确实是个钢铁直男,可见 ani 这种群体,已经碰过形形色色非常多的人,对于Ivan这种,她可望不可得,而对于igor这种,短暂的,缓慢的示爱,并且没有对她的身体充满非分之想,她反到对这种人感到厌恶,导演可能是想表达,对于这种职业的群体,这些sexworker,她们因为长久的出卖身体来接触人,从而对感情的看法已经逐渐改变了,她们会发现,自己除了奉献出身体所外已经拿不出自己的爱,甚至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毫无价值。 所以导演这最后一场戏, igor 偷来了 ani与Ivan 的结婚戒指,这是ani对于爱情的向往,她从一开始的只想要money 从而真正体会到 结婚的幸福,甜美感情的愉悦,这是她作为一名sw从未得到的,她到后来并不是单纯的想嫁进豪门,而是那段真实的感情让她无法自拔,不然她并不会毅然决然的离婚,并且看透了一切。 这个戒指对于ani来说,是结婚后炫耀的资本,是对sw这份工作的脱离,对爱情的向往,对未来的憧憬,却唯独没有看清自己,sw需要看清自己在社会的地位。ani 麻木了,沉浸在幻想里。 igor 将她的行李拖上了ani的家门口,回到汽车 , ani 并没有下车,她看向igor ,熟练的坐上了 igor的腿,放低座位,熟练的脱和动,甚至熟练的将igor的手放到自己的臀部 , igor 就那么看着ani,igor 绝对爱她 , 她甚至拉着 ani 的头想轻吻。 俗,依旧是俗, 这一幕不知道俗哭了多少人。 ani在抗拒,她抵抗这个吻,她奔溃了,趴在igor的胸口流泪。 她发现自己仍然是个SW,即使结婚了 ,在别人眼里依然是hooker,是个三陪,同她结婚的Ivan都称她为三陪工作者,他只把她当个玩具,工具,而并非真正爱的人,爱的妻子,他与她结婚不是因为爱,她与他结婚也并不是因为爱,却幻想成爱,她混淆了自己的地位,忘记了自己身上的标签。结婚使她疯狂幻想,执迷不悟,离婚让她回归现实,而她坐上igor大腿的那一刻,她突然认清了自己,是的,她依然是哥sexworker,即使igor如果是真的爱她,她依然把他当做成了顾客一般,她奔溃的,绝望地留下了眼泪。此时她哭的不是这段短暂的婚事,而是她重新认清自己的身份后,想起还要做起之前的工作,嫉妒她的同事对她说的她的婚姻不会超过两个星期也应验了,哭自己的执迷不误,哭自己的职业改变了她整个人。
通过 anora 来介绍 sexworker 这部分群体 , 很多人对最后爬上大腿这部分感到不适,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觉得应该让 ani 拿上戒指然后走就是了 , 为什么要这样呢? 最后的ani奔溃确实是点睛之笔,躲在房间奔溃自然没有她在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时奔溃对她这部分群体来的讽刺大。
贴上些豆瓣影评:
Marla Cruz原文:Romance Labor: on Sean Baker’s Anora
从十个月前的金棕榈到昨天的奥斯卡,肖恩·贝克和麦基·麦迪森一直在一次次获奖感言中感谢性工作者群体(sex workers,以下简称SW)的存在,说这部电影是献给ta们的。所以SW怎么看待《阿诺拉》这部片呢?
我碰巧读到了一篇从业多年的美国SW对于《阿诺拉》的评论,许多观点和切入视角都蛮有意思。
上来先说说作者MarlaCruz的结论吧:她认为《阿诺拉》对于SW生活境况的描绘“有一英里宽但只有一尺深”,也就是说,肖恩·贝克的刻画肤浅失真并且将SW主角视为客体,因此也强化了社会对于SW群体陈腐老套的刻板印象。
所以《阿诺拉》具体失真在哪里?作者指出的第一点是片中的Ani没有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职业人格,而这本应是一个SW为了平衡工作与生活所做的基础准备:“为客户提供情感服务的SW往往会为自己制造一个职业人格,以便在我们的真实感受与我们想让客户获得的感受之间设立心理缓冲地带。”而片中的Ani完全没这么做:她在夜店里使用自己真名,她把自己的真实人格暴露在客户面前,她为富二代男孩Vanya饰演欲求不满的美国女友,却很快就让自己陷入了这段虚假剧情。这份缺乏自我保护的天真诚恳在作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作者指出的第二个失真点是Ani的粗心大意:她完全没考虑到Vanya的父母以强力措施迫使她取消婚事的可能,因此也没有对此可能性做出任何防备。她毫无忌惮地与Vanya高调出入各类场合(比如片中提及的NBA比赛现场),她想都没想过要询问她和Vanya居住的豪宅的业主是谁,这也导致了后来她在“自己家中”被绑架的局面。
作者对此评论道:“我本以为一位在夜店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女人会知晓我自己凭多年经验明白的道理:在这个行业中,几乎没有犯错余地,一瞬间的大意就会使我们付出惨痛代价。迅速且精准的洞察力是我们最重要的防线,抵御着那些无时不刻在探测我们弱点的客户。这一课,许多SW在入行早期,就通过亲身经历,或是对于同行所遭受的虐待、剥削甚至死亡的见证而领教过了。”
“……但当Ani收拾行装离开夜店时,周围同事对她的新婚竟然一致祝贺。我很难想象在曼哈顿——这个被资本及其固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所定义的世界中心——居然没有同事意识到她这段婚姻中存在的严重权力失衡,及其可能为Ani人身安全带来的危险。”
作者也指出了几个相关的可疑细节:一个在曼哈顿从事服务行业多年的人,大概率已阅尽富商名流,被Vanya这个级别的富商之子及其财产冲昏头脑的可能性其实不高;此外,打手Igor在故事临近结尾的段落里对Ani说“我更喜欢你的真名Anora”的台词让她看了想吐,因为这种话术基本上是男人想要和SW迅速拉近距离时使出的最廉价伎俩。
讲完了失真之处,现在来讲讲“客体化”问题。作者是和一群普通观众一起在影院里看的《阿诺拉》,因此她提及了影片在呈现方式上让她不舒服的几个点:
1. 把Ani对三位打手的反抗表现得过激且可笑。这与影片采取的视点和叙述方式有关:在那场客厅绑架戏里,贝克并没有采取Ani的视角来呈现此场景对她而言的恐怖本质,而是更多地采取全景镜头视角,并将打手们塑造成无能笨拙的傀儡,使得整场戏看上去像一场滑稽剧。
整段戏里的一个细节唤醒了作者的回忆:当Igor临场发挥,顺手拿起电话线将Ani的手反绑在背后时,作者想起了一位客户在钟点已满后依然试图把她强留在房间里时的眼神——他一边抓住她的胳膊一边用眼睛扫视整个房间,试图临场找到能把她彻底制服的趁手物件。但当这个细节在影院放映时,绝大多数观众却在笑。或许一个衣冠不整的女孩试图“歇斯底里地”反抗比她块头大一倍的男人的场面,的确很好笑吧。而这种对Ani缺乏共情的观看感受,无疑是被贝克的呈现视角所塑形的。
2. 对Ani肤浅老套的刻画。Ani似乎从本质上蔑视自己的工作。自从成为临时女友后她就有些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身份,沉浸在娇妻式的虚构角色中;在与Vanya结婚后她更是对他人提及其前身份的做法感到强烈不满。到最后,当一切竹篮打水后,她能想到的对“岳母”最有力的报复话语是:“你儿子是如此恨你以至于专门娶了个妓女来气你。”
所以Ani梦想的本质是什么?不劳而获的阶级跃迁而已。或许她的梦想中存在更多动机,但贝克对她的刻画过于潦草,以至于没有为这种可能性提供证据。这个角色无法引发观众的深度共情,与她的肤浅形象和半熟心智有紧密关系。作者在此处写了句精辟锐评:“这个角色更像是砍杀片里第一个被杀掉的愚蠢荡妇,而不是《风月俏佳人》里面被客户的柔情体贴所俘获的主角。”
Ani哭闹喊叫了大半场电影,但直到她失去一切、破碎无助时,影片才开始邀请我们与她共情。作者评论道:“Ani本该走出最后那辆车,回到自己房间,用她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慰藉自己——吃东西,睡眠,或者哭泣。她已经太久没有拥有过独处和隐私的权利了。”
然而肖恩·贝克做了什么选择呢?他让Ani在看到Igor为她保留的婚戒后爬上了对方的大腿。
于是观众在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了Ani的破碎一面。
但这其实是对社会刻板印象的最糟糕重复:“SW们粗俗、愚钝、冲动、性欲过强,只有在受苦受难状态下才最能凸显出人性。”
所以这样的刻画会导向什么呢?让社会继续将SW群体固定在已经足够边缘化的位置。
作者在最后做了几句精辟总结:“In Anora the sex worker is exactly who society thinks she is. 这部电影体现着老套的且去人性化的消费者幻想:SW是如此热爱客户,以至于她混淆了奉献与劳动、自我身份与工作身份之间的区别。”
题外话:作者提及的另一个不可信设定——Ani在被“岳母”威胁了几句后立刻登上了去内华达的飞机的桥段,在我看来也非常不成立。作者展开讲了下她的疑惑:“Ani到底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筹码?她之前为一个她刚认识十天的男人抛弃了自己的整个生活。”当赌注变大而筹码依然微乎其微时,Ani却突然丧失了一直保持至今的斗志,这个无力的转折不该是一部奥斯卡原创剧本获奖片应有的水准。
个人而言我很喜欢肖恩·贝克的几部前作,单纯拿床戏多来批评《阿诺拉》男凝剥削也蛮可笑的。但这部电影确实没有体现出一丁点贝克在《橘色》和《佛罗里达乐园》里对少数群体体现过的爱意,也没有鲜活地表现出这些角色的梦想和热爱。如果他打算沿《阿诺拉》的创作线路继续走下去,那他的后续作品确实不看也罢。
从《可怜的东西》到《阿诺拉》:骂伪女性电影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6310091/
1986年的独立电影《Working Girls》讲了性工作者的一天:上班,接客,不接客时接电话,跟同事(其他性工作者)聊天、拌嘴、吃外卖,在老鸨来视察前飞速打扫没吃完的烤鸡盘子,跟老鸨吵架(像极了跟老板吵架),下楼买药时要给好几个同事捎避孕套(像极了今天买奶茶顺便给同事带),因为偷接私人电话被老鸨炒鱿鱼,在老鸨要求加班时拒绝最后被迫接受,在客人那受气后放下狠话不干了(可能第二天还会回来),终于上完班后归心似箭,踩上自行车一路闪电回家,不忘给同性爱人带一束花表达晚归的歉意。——这是性工作者作为人的“生活”。
肖恩·贝克所谓的关怀性工作者:暗示她的移民身份暗示她的穷苦但不给出任何个人历史。而对于她的“现在”,也只窥伺她“工作”的样子,用俯视镜头拍她全裸,换着花样和角度拍她提供性服务,摄像机紧紧追着她跳舞时的臀部,比男主角的视线贴的还紧,拍她除了“fuck”几乎不会说别的话,临结尾了,让她梦醒,面对一个大块头男的示好,又是腾地坐到他大腿上开始取悦。——这是肖恩·贝克对性工作者作为一个符号的刻板想象。
——难道性工作者就没有个人生活?就是24h激情上班?难道她们跟这个世界连结的方式就是坐到所有对她好的人的大腿上去?这是怎样狭隘又自以为是的刻板想象。她下了班住在哪里?跟谁往来?电影倒是告诉我们她住布鲁克林铁路旁边,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肖恩·贝克不在乎。他只是借用了“性工作者”这个名头讲一出他以为的消费社会批判。他不关心这些人的身体、灵魂和命运,却无耻借用了她们。 肖恩·贝克心中的“同情之理解”性工作者=你看她很认真、专业、努力地提供着性服务和情绪服务。这种所谓“合理化”的最大问题就是用“专业性”遮蔽了“人性”。上文说到的《Working Girls》有两个细节——女主在接待每个男客时都会把毛巾递给他们说“Please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暗示他们自己脱衣,这种小小的体面是她从业中保留主体性而形成的习惯。另一个细节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精英男在精神上践踏女主,大意是“你以为你装得挺体面你就不是妓女了?”女主虽然不能推开他,但还是恨恨的神情,之后想着辞职。这些色情镜头完全不色情,它让人感同身受那种活生生的人被践踏的耻辱。性行业不是《阿诺拉》和《可怜的东西》里那样女主无坚不摧地“嫖了男人”,只把男人当工具,那里比任何工作更甚地有着剥削、欺压和践踏。我越是同情之理解性工作者,就越不能忍受白男导演对这个行业的想当然和以此为名的大拍特拍裸戏。 【补:才知道《阿诺拉》拍性场面甚至没有用亲密关系调解员intimacy coordinator,因为导演让米奇和男演员来决定要不要——他们敢说要吗?导演处于权力关系中的上位,且演员考虑到日后合作也有“证明自己professional”的压力(来源:https://variety.com/2024/film/news/anora-intimacy-coordinator-respond-mikey-madison-sean-baker-1236254012导演连女演员的正当权益都要“我让你选择一下”,就类似于休产假是正当权益然后老板让你选要不要休。还大言不惭关注底层性工作者,这很白男。】
《阿诺拉》的肤浅让我在电影院如坐针毡。但最可怕的是摄像机对女性身体的暴力——银幕射来的结结实实的身体和精神的疼痛——就像《新女性》里韦明看到酒吧地板上被拖行的女奴仿佛看到了自己,当《阿诺拉》不断切到大全景中赤裸的扭动的阿诺拉,又切到阿诺拉F word的嘴巴的大特写时,我感到摄像机在强暴我——强暴所有女性。
这种疼痛在《阿诺拉》广受好评的结尾处转变为纯粹的恶心。当Igor载着阿诺拉停在纽约的漫天大雪中,Igor掏出偷偷保留下来的阿诺拉的钻戒时,我在心中默念“不要吧,不要吧,不要”——然后,他们还是开始了(唯有白眼)。
电影在这里做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区分。从豆瓣短评看,它触动了很多人——作为脱衣舞女的(阿诺拉本人反对被称为“妓女”)阿诺拉直觉性回报Igor善意或爱意的方式是,坐到他的大腿上开始取悦,而Igor则直觉性地想要吻她。不习惯“非交易性”亲吻的阿诺拉本能地反抗,拍打Igor,最终放松下来,沉浸在他的吻中(…?)——Igor的爱“救赎”了阿诺拉——打出这段话时我感觉自己在写十年前的晋江狗血言情。而这个情节竟然是一部金棕榈奖电影的结尾。
【在别处收到一个评论更正“阿诺拉根本没有“沉浸在Igor的吻中”,她甚至都没有接受他的吻。Igor捧住阿诺拉的脸试图去吻她,结果她十分抗拒,最后因为自己无法接受Igor对自己真挚的感情直接趴在他怀里哭了,俩人压根就没吻上。”特补充在此。——在这段时间的思考里我也意识到结尾的十分钟可能没那么强调“爱的救赎”——但我最在意的点还是——如果只是底层的互助和安慰,到结尾处停下车就好了。两人前一晚的沙发谈话已经很好了。非要让阿诺拉“职业性”爬到他身上取悦一次而Igor回应以吻,仿佛从事脱衣舞职业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永远只会着一种交流的方式。这种对性工作者的刻板想象,用职业标签化一个活生生女性个体的“叙事技巧”,我还是认为问题很大。】
它一点也不“救赎”。它令我作呕。
如果说《可怜的东西》作为伪女性电影的逻辑是“女人的性长久地被以爱为名的家庭和生育责任所束缚,所以性欲的解放等于女性的解放”,那么《阿诺拉》只不过是硬币的另一面——“阿诺拉的爱和性长久地在新自由主义明码标价的市场交换中被分割,所以当天使般的Igor引导她将爱和性再度联结起来时,性工作者阿诺拉得到了救赎”。
问题不在于这种逻辑在具体情境中的变化——如人们会基于《可怜的东西》争论如果贝拉就是享受性,那么她以妓为营生是不是“竟是她嫖了男人”的解放——问题在于,如果爱和性所谓“原初”的统一源自前现代社会男性对贞洁女性的期待,那么爱和性今日所谓解放性的分离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将女性身体再次商品化的前提,这两种逻辑本质是都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创造的衡量和评判女性身体、欲望和关系的价值体系。
重要的不是分离还是合一,而是谁在要求分离?谁在要求合一?谁在教导我们关于何为“原初”与何为悖逆的知识?谁在给分离或合一上纲上线上价值?谁在评判和惩罚着那些不服从这些价值体系的女性?《阿诺拉》浪漫化为资本主义飞雪漫天中唯一温情的这抹车内的“爱性合一”,在嘲讽了后者的同时,只不过是回归了那个前者同样规训性质的原初神话。
它不过是暴露了白男导演肖恩·贝克匮乏的想象力——他根本无法想象以上陈词滥调以外,女性对世界的欲望,以及女性和世界联结的方式。或许,他根本不能想象女性可以自我救赎。当他用所谓荒诞喜剧的语言让《阿诺拉》中每个人都丑态百出、“类人群星闪耀”时,当他不厌其烦地拍摄他口中的希望为之发声的弱势群体——性工作者——阿诺拉的“工作”中的裸体以及连珠炮似的喷射的“motherfucker”时,他并没有给出任何有新意或深度或力度的批判——不是用镜头疾速扫过俄罗斯富豪的纽约豪宅,脱衣舞夜店的光怪陆离,然后配上疾速的音乐,就是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了——这件事,甚至一百年前的电影都做得更好。
如果对《可怜的东西》的批评可以用“除了性欲,女性还有多种多样、丰富、炽烈的欲望”,那么对《阿诺拉》的批评正好可以是“除了男性能想象的那种男女之爱,女性还有多种多样、丰富、炽烈的爱世界的方式”。她不需要男性教会她“爱”。
这也是为何我会为《婚姻故事》中很快给离婚后的斯嘉丽·约翰逊安排了新情人而失望(尽管《婚姻故事》的两个主人公都是经典的新自由主义欲望主体,所以这种情节设置倒是很现实主义),却会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结尾处女主的孑然一身而感动——如果性不是女性的救赎,那么某个男性的爱也不是,至少不一定是——尽管《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导演最倾注了全部同情的,还是女主的前男友。
我感到恐惧的是,像《可怜的东西》和《阿诺拉》这样的伪女性电影愈是成为电影节的宠儿,此类电影便会愈多。但不知从何时起,在观看它们的过程中所接收的暴力,令我甚至不愿轻易去看。当摄像机对准某人的身体,那本身就是暴力。创作者应该用电影的其他部分去抵消这种暴力,或者至少让这种暴力有其价值——可惜,它们往往只是借助了女性的身体,turn her-story into his-tory.
《女性瘾者》刚上映时惊世骇俗。那位为了追逐性欲而主动成为坏妻子坏妈妈的Joe俨然女权先锋,结尾处石破天惊的一枪足以传世。有趣的是,作为Joe对照的女友在坠入爱河后停止了放荡不羁的生涯,并对愤怒的Joe说“你以为你懂得性的一切吗?性的终极秘密是,爱”——Joe不屑地摔门而去——“性爱分离”和“性爱合一”的老调重弹。
然而,在Joe直白地称黑人为Negro表达对政治正确的蔑视时,我分明在她身上看到了拉斯·冯·提尔的自我投射。他的厌女以及厌女以外的种种黑历史,无需赘述。当我带着“Joe是他的自我投射”的角度再次观看《女性瘾者》,我便发现了种种可疑之处——
例如,当Joe在家中自行堕胎时,夏洛特·甘斯布的表演令人心碎,令人感慨女性为自由需要多付出的代价,但拉斯·冯·提尔竟像不满足似的,补充了一段似乎根据超声图像绘制的动画示意——胎儿被尖锐的器具勾出宫颈。一个极其疼痛但叙事上毫无必要的插入。
在这个例子里,拉斯·冯·提尔将自身不可公开的反人类欲望投射至女性角色身上,却对她的疼痛毫无怜悯,反将其美学化,将她的苦难转化为大众观看的对象。我甚至不惮于想象他在插入这段动画演示时,会沾沾自喜,正如他不厌其烦地在章节体电影中插入众多关于数学、文学、哲学和宗教的引用。反而是到了《此房是我造》里,他对同为他自我投射的男杀人狂杰克极尽赞美和同情,甚至在结尾处让他在天国和炼狱中来了一段高光自陈。
这种对女性身体、女性体验和女性世界的无知、冷漠和“美学化”,往往可以冠以“反映真实”的名头——肖恩·贝克或许会说,我用剥削性的方式拍摄阿诺拉扭动的裸体,是因为我要让电影院的你被吸引,然后反思是否你也是消费她身体的体系的一部分。对这样的“艺术声明”,有无数可行的质问和反击——“非如此(剥削性)不可吗?”,“现实果真就是如此吗?”正如《可怜的东西》里,裸露可以被辩护,但种种极其诡异的机位和角度则分明暴露了导演一贯热衷的猎奇恶趣味。
但质问的尽头是——他们不会觉得那是问题,因为那对他们——精英、白人、男性——从来就不是问题。我可以坦荡地、真诚的、大声地说,我没有被阿诺拉的身体吸引——事实上,每当高速镜头猝然转到Ivan随时随地发情而阿诺拉极尽讨好,我知道肖恩·贝克希望我跟着他的摄像机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异化下人的动物性——我就会翻个白眼低下头。我不是消费她身体的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我没有被她的身体吸引并不妨碍我持续反思他声称非得如此才能被反思的——那个体系。而那个体系正日益虚拟化为此类图像的无限繁殖和流通。
我评价不了多少分,反正我不喜欢,国家不同,社会不同,无法共情,拍成这样拿奖,我感觉更适合拍成个纪录片的了,拍成个滑稽的不现实的电影就真的很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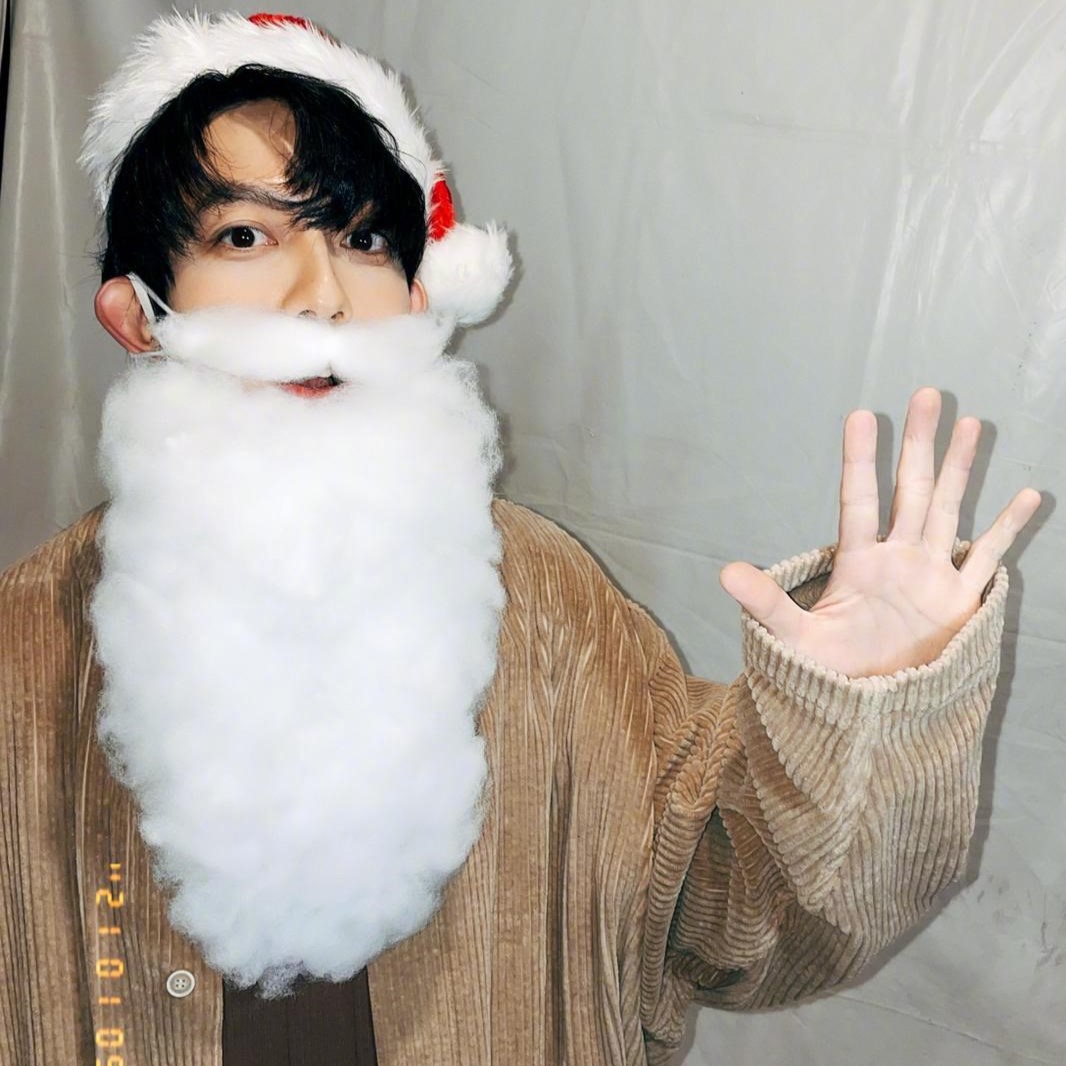
Comments | NOTHING